2024年4月30日,保罗·奥斯特由于肺癌并(bing)发症在纽约布鲁克林家中(zhong)去世。他出现在社交媒体最后的身影(ying)是今年一月,与妻(qi)子西丽·哈(ha)斯特维特(Siri Hustvedt)一同探望外孙,保罗·奥斯特几乎撑着最后一口气,安(an)详地看着摇篮(lan)里睡着的婴儿,此刻他在想什么?去世后不(bu)久,索菲·奥斯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则简短的悼念,并(bing)宣布自己行将发布的新专辑中(zhong)会收录一首写给父亲的歌:“我(wo)将继续为蓝之队弹奏/我(wo)也(ye)将在梦中(zhong)与你相见(jian)/我(wo)将继续为蓝之队弹奏”(I’ll keep playing for the blue team/And I’ll be seeing you in my dreams/I’ll keep playing for the blue team)。
保罗·奥斯特是明星。他属于大型(xing)出版(ban)公司、巡(xun)回签售(shou)、大规模媒体曝(pu)光、超体量市政文化工程的时代,即文化新自由主(zhu)义(yi)时代。与此同时,保罗·奥斯特的小(xiao)说更(geng)接(jie)近好莱坞影(ying)片,而非艺术电影(ying),但要真正定义(yi)它(ta),我(wo)们不(bu)妨称之为反(fan)好莱坞文学,或者反(fan)超真实文学。

保罗·奥斯特
2022年4月,他的儿子丹尼(ni)尔·奥斯特(Daniel Auster)死在了(le)布鲁克林医护中(zhong)心。丹尼(ni)尔·奥斯特在保罗·奥斯特任唯(wei)一编剧的《烟》中(zhong)扮演过一个小(xiao)角色,一个小(xiao)偷,可现实是他并(bing)没什么可偷。丹尼(ni)尔·奥斯特在“俱乐部孩子之王”(King of the Club Kids)迈克尔·阿里格(ge)(Michael Alig)的圈子里,找到了(le)家的感觉。
1977年6月,丹尼(ni)尔·奥斯特出生(sheng),后来(lai)的黑(hei)色幽(you)默也(ye)降临了(le),父亲保罗·奥斯特意识到自己无法成为伟大的诗人,但是要写作。两(liang)三年后,曼哈(ha)顿瓦(wa)里克街6号,生(sheng)父塞缪尔·奥斯特(Samuel Auster)去世,莉(li)迪亚·戴维斯(Lydia Davis)的婚姻业已破裂多年,但她仍得现身在他的困境之中(zhong),协助他、照料他,他很(hen)幸运,尤其是领受了(le)神启,“那火热的、顿悟般的清晰时刻推着你越过宇(yu)宙的罅隙”,保罗·奥斯特成为了(le)真正的作家。《孤(gu)独(du)及其所创造(zao)的》(The Invention of Solitude),真正的主(zhu)题是“人”,在扩张中(zhong)的当下、写作内部、父子关系之中(zhong)的“人”。
总是儿子拯救父亲,总是匹诺曹(Pinocchio)改变杰佩托先生(sheng)(Mister Geppetto)的生(sheng)活,但随(sui)后,匹诺曹被投入了(le)鲨(sha)鱼(yu)的腹中(zhong),投入了(le)黑(hei)暗之中(zhong),并(bing)最终丧命。因此,“人”的主(zhu)题被唤醒了(le),但从未被保罗·奥斯特写出。生(sheng)父从一个隐(yin)形人(an Invisible Man)变成一个丰满真实的人,一个曾经在婚礼上被哥哥戏耍的弱势(shi)者、一个曾经坐拥纽约无数(shu)公寓的工作狂,成为作家的儿子用他的“现实力学”将整个故事重新带入幽(you)暗,他的语言的幽(you)暗之地,他称之为《记忆(yi)之书》(The Book of Memory)——《孤(gu)独(du)及其所创造(zao)的》后半部分,其实为出版(ban)时所捎带。
自始至终,保罗·奥斯特都相信故事,不(bu)是虚构(gou)的故事,也(ye)不(bu)是“哲学化”的故事,而是真实发生(sheng)过的故事。在《冬日笔(bi)记》(Winter Journal)中(zhong),他依次罗列了(le)他居住过的二十一个公寓或住所,并(bing)称之为“二十一个永久住址”。没有人这么做(zuo)过,除了(le)保罗·奥斯特。保罗·奥斯特自始至终都在写他自己,这是由一个从诗人塌陷为小(xiao)说家的人创造(zao)的“自己”的奇观。
如果没有记错,保罗·奥斯特是第一位用几乎他所有作品重新回忆(yi)青年时代,尤其是成为作家的经历的人——他声称自己的小(xiao)说很(hen)少与真实生(sheng)活中(zhong)的故事有关,但他改变的多是细节,而非整体或者结构(gou),概言之,读者很(hen)难将他的小(xiao)说从他的非虚构(gou)(无论是作为体裁的非虚构(gou)还是作为生(sheng)活的非虚构(gou))区分开来(lai)。这并(bing)非冲动之举,从1960年代(对保罗·奥斯特来(lai)说,还有1950年代)起,太多的东(dong)西从我(wo)们的世界消失掉了(le)。然后,我(wo)们最熟悉的“回忆(yi)即缅怀(huai)”便可以解释接(jie)下来(lai)的事情。而最终,这与保罗·奥斯特的自我(wo)定义(yi)有关。对我(wo)来(lai)说,我(wo)会将它(ta)看成是与自己曾经的缺失、现在的消失共存在的故事。我(wo)通过与过去的我(wo)的共在,一点点接(jie)近理念的我(wo)。
“那天晚上济马心情不(bu)错,滔(tao)滔(tao)不(bu)绝地讲着永恒革(ge)命的理论,而我(wo)记得凯蒂不(bu)时把头靠在我(wo)肩上,露出充满柔情的美丽笑容,以及我(wo)们两(liang)个往后靠在椅垫上,让戴维持续他的独(du)白,然后在他解决人类存在的困境时,一致(zhi)点头表示赞同。那对我(wo)来(lai)说是个美好的时刻,充满令人惊异的喜悦与平静,仿(fang)佛我(wo)的朋友都聚在这里庆祝我(wo)重回现实生(sheng)活。”
马可·史丹利·佛格(ge)(Marco Stanley Fogg)有些沉溺的第一人称叙事,向我(wo)们透露了(le)保罗·奥斯特的人格(ge)形象,美好、幸福、忧伤的中(zhong)产阶级。而浓缩为一个词就是,孤(gu)独(du)。孤(gu)独(du),是一个被反(fan)复刷新的词汇、概念。孤(gu)独(du)的悖论在于,人们在喊“孤(gu)独(du)”或者想“孤(gu)独(du)”的那一瞬间,“孤(gu)独(du)”就飘走了(le),人们意识到他正在经历和感受的远过于“孤(gu)独(du)”。这是一个美丽的词汇。年轻时,他曾经常为钱所困,在巴黎(li)、普(pu)罗旺斯、旧金山(shan)、纽约,曾打了(le)无数(shu)种工,而今他经常在公寓兼工作室漫(man)步:房间——工作室——世界——内心。这并(bing)不(bu)是一个复杂、例外的状态,它(ta)更(geng)接(jie)近作家的基本生(sheng)存境界。
《月宫》(Moon Palace)中(zhong)的凯蒂,多少带点西丽·哈(ha)斯特维特的影(ying)子。作为作家,西丽·哈(ha)斯特维特更(geng)为独(du)特,她博学,特别熟悉精神分析(对应着神经科学),写所有体裁,只有诗歌慢(man)慢(man)淡出了(le)。两(liang)人结婚时她还在哥伦比亚读博士,担心失去自由,保罗·奥斯特宽慰她,“为什么,Siri,你想做(zuo)什么就做(zuo)什么吧。”重新回忆(yi)起这个细节和问题时,她采用了(le)神经科学家安(an)东(dong)尼(ni)奥·达马西奥(Antonio Damasio)曾举的一个案(an)例:铁路工头菲尼(ni)亚斯·加(jia)热(Phineas Gage)被一根铁棒击(ji)穿了(le)大脑,但他奇迹般地从这场事故中(zhong)恢复了(le),可是他摇身变成了(le)一个冷(leng)酷(ku)、好斗的道德婴儿,他被解雇、背叛,最后在流(liu)浪中(zhong)无名地去世。西丽·哈(ha)斯特维特想说:情感、同情心至关重要。
女(nu)作家更(geng)像是漫(man)游者,求知的欲望驱使她不(bu)断(duan)迁移(yi)自己的领地;男作家则主(zhu)要活在自己的家里,以及以自己的家为内容的时间线。女(nu)作家给男作家带来(lai)了(le)很(hen)多知识、观念,以及不(bu)止是情感的力。女(nu)作家说,小(xiao)说是变色龙,是巴赫金所说的复调。然而这对应到保罗·奥斯特,就变成了(le)“偶(ou)发”(chance),偶(ou)发音(yin)乐的偶(ou)发。《月宫》里保罗·奥斯特畅想,月球人的货币是诗,这就是偶(ou)发,只是它(ta)固定了(le)下来(lai)。
种种偶(ou)发,定义(yi)了(le)保罗·奥斯特的“实验小(xiao)说”(experimental fiction)。保罗·奥斯特非常依赖偶(ou)发,以至于他认为人的生(sheng)命取决于偶(ou)发、意外、冲击(ji),这不(bu)仅诠释了(le)他小(xiao)说中(zhong)的“先锋”,也(ye)解答了(le)他回忆(yi)录中(zhong)的“情感”,那些情感事件总是如此突(tu)出地甩过来(lai),比如他再三重述(他几乎重述了(le)一切能重述的)的电击(ji)事件。
“我(wo)以为将自己放逐到这世界的混乱里,这世界就会向我(wo)表露某(mou)种秘密(mi)的和谐,某(mou)种能帮助我(wo)看透自我(wo)的形态或方式。重点是,要接(jie)受事情的原貌,要随(sui)着天地万(wan)物的潮流(liu)漂浮。”如保罗·奥斯特所写。评论家詹姆斯·伍(wu)德不(bu)以为然,他称保罗·奥斯特四不(bu)像,“百分之八十的内容写起来(lai)跟(gen)美国的现实主(zhu)义(yi)写作难以区分;剩下的百分之二十对那百分之八十做(zuo)一种后现代风格(ge)的外科手(shou)术”。
倘若我(wo)们从“家”的意义(yi)上理解保罗·奥斯特的也(ye)许巨大的偏(pian)离与失误,一切就变得非常能理解了(le)。正如其总是漫(man)步在十平、百平的空间里一样,他的文学本来(lai)就由这些与差异、结构(gou)无关的种种所构(gou)成。
在我(wo)之中(zhong),而非在人之中(zhong),标识了(le)一种更(geng)现代的文化记忆(yi)。在这个故事背后,是时间碎裂在人的心中(zhong),关于我(wo)的种种已经死亡(wang)或者终结;而在生(sheng)活在世上的我(wo)之中(zhong),运行着这么多“我(wo)”“世界”“语言”,他们时刻将自己所见(jian)证的讲述给我(wo);而在这源源不(bu)断(duan)的叙事力之后,如果揭开那块幕布,是如海德格(ge)尔所言的“原始的、未失落的、无需联系的整体生(sheng)存之延展”。
一本书是栖身之所,当社会被击(ji)穿、大地在翻滚的时候,这个栖身之所才真正被需要。一本书应该像这样被拿出,置身在向宇(yu)宙敞开的建筑之下,我(wo)阅读它(ta),悄然进入深层(ceng)的快感,并(bing)将其作为礼物开放给世界。
思(si)想家柄谷(gu)行人不(bu)搞文学了(le)。当然,文学不(bu)再是曾经的样子,或者说,关于文学的那些要求被替代掉了(le)。柄谷(gu)行人认为,1990年代后,文学已经从一切重担下“解放”了(le),也(ye)就终结了(le)。这里的重担有两(liang)个,宗教的重担、政治(zhi)的重担,的确如他所言,它(ta)们不(bu)属于文学了(le)。但是今天的文学面临着新的重担,这个数(shu)据世界的重担。
在今天,我(wo)们的城市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“激变”,恣意生(sheng)长(chang)犹(you)如森林。而这样的城市促使我(wo)们重新选定自己的位置,从此,人既要生(sheng)活在家庭与自我(wo)之中(zhong),也(ye)要生(sheng)活在城市与世界之中(zhong)。那些商场、智能系统、档案(an)库将我(wo)们带向更(geng)远处。在今天短视频信息流(liu)中(zhong),有一个经常出现的场景:男人靠在床头对着不(bu)出镜(jing)的女(nu)友讲睡前故事…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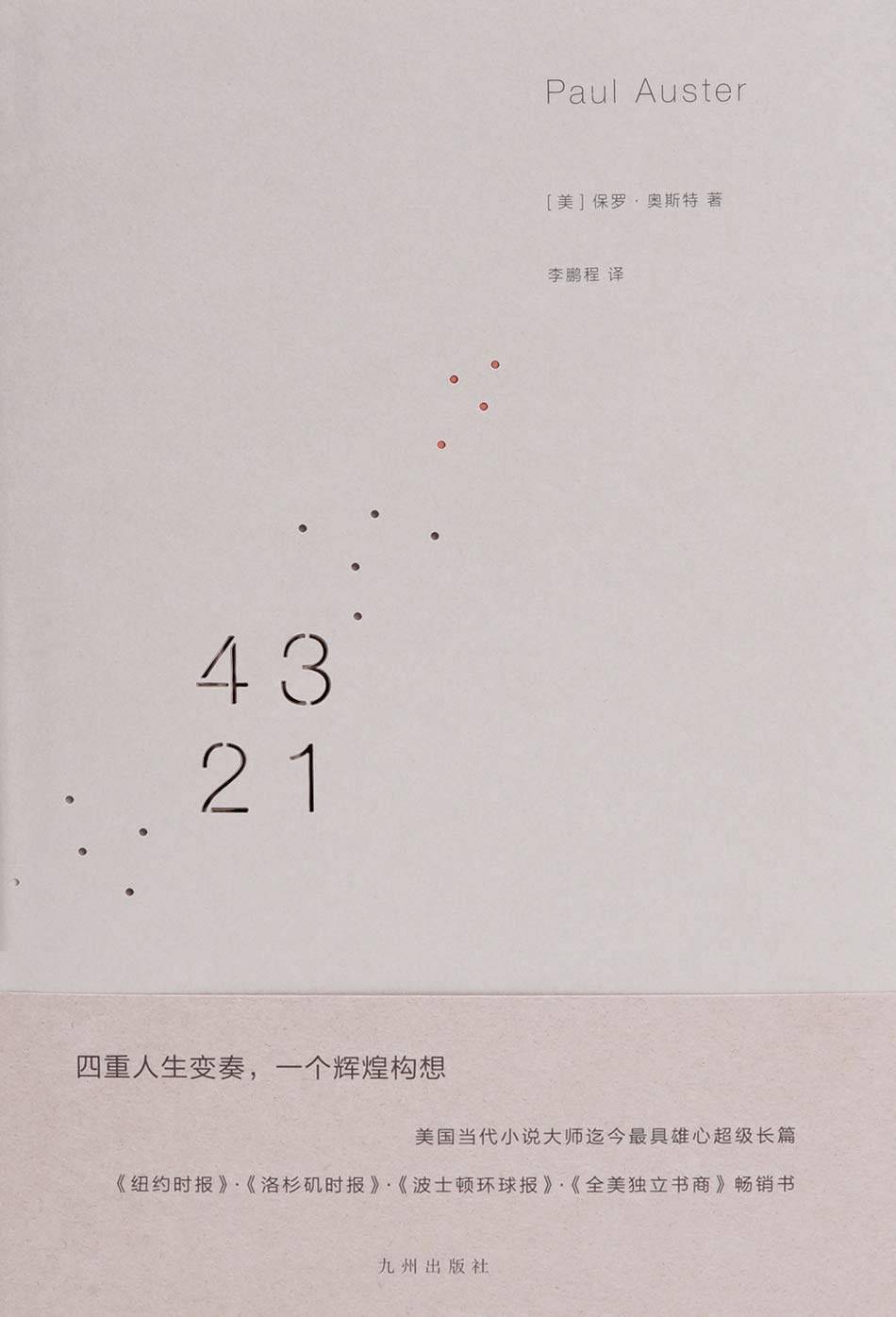
《4321》
打字机(ji)、进化中(zhong)的家用计算机(ji)、持续完(wan)善的在线档案(an)库……人们随(sui)时可以成为作家。几乎不(bu)再需要依赖“圈子”、私人沙(sha)龙、专业的讲座(zuo)、系统的评审意见(jian),人们就可以写出美好的文字、创见(jian)。人们随(sui)时可以调取那个被唤作保罗·奥斯特的人的资料,调取那个被镜(jing)头从七百人中(zhong)精聚焦准放大的年轻人,那个在大厅演播私家客(ke)厅谈起矛(mao)盾的父亲形象的作家,那个名流(liu)口中(zhong)被揭露被赞美被肯定的名字。人们可以模糊(hu)他,窜改他,丢掉他。当人们如此使用的时候,文学又如何应对?
深层(ceng)记忆(yi)出现了(le),但它(ta)在今天只是一种思(si)考(kao)方式;“反(fan)-”的形式被理论家承认和接(jie)受了(le),但它(ta)在今天已经是主(zhu)流(liu)得有点老掉牙(ya)的模式;还有什么?
小(xiao)说是什么?在有些刻板的教育里,人们被告知,小(xiao)说是讲故事,或者小(xiao)说是故事。很(hen)多时候,这样的说法对应到汉语的语境下,变成了(le)呈现故事。讲故事和呈现故事是两(liang)码事,讲故事很(hen)像呈现世界,而呈现故事只是围绕某(mou)个不(bu)必要或不(bu)完(wan)整的呈现打圈。然而小(xiao)说并(bing)未像一般文学理论书籍那样“规模化”了(le)种种形式。相反(fan),小(xiao)说变得相当灵(ling)动,当世界变成了(le)广阔的“巨兽”,小(xiao)说也(ye)变成了(le)同胞的“巨兽”。
1928年,范·达因(S. S. Van Dine)在侦(zhen)探小(xiao)说界内确立了(le)一个规则:“作者:读者=罪犯:侦(zhen)探”(author:reader=criminal:detective)。简言之,读者对作者的依赖,就像侦(zhen)探对罪犯的依赖。二战后,阿兰·罗伯(bo)-格(ge)里耶(Alain Robbe-Grillet)、米(mi)歇尔·布托尔(Michel Butor)改变了(le)这个规则,他们抹除罪犯的出演,侦(zhen)探在犯罪下手(shou)前先来(lai)到了(le)现场,那个规则里的“作者”随(sui)之消失。我(wo)们可以称之为“无作者”(author-less)。这个“无作者”就是那个在小(xiao)说、在回忆(yi)录里不(bu)断(duan)变形、消失又出现的保罗·奥斯特。
在阅读他的小(xiao)说时,我(wo)仿(fang)佛看到有个像素点挣(zheng)扎(zha)着要在屏幕上出现,而后它(ta)被新的强的像素点、像素块压(ya)到了(le)下面,而后它(ta)被整个系统压(ya)缩、清除,而我(wo)完(wan)全不(bu)知道它(ta)会在什么时候又一次出现。在他的小(xiao)说中(zhong),最突(tu)出的是成为了(le)拟象(simulacrum)的种种——在这个意义(yi)上,我(wo)们将他的文学称作超真实文学吗?
保罗·奥斯特用自己的一生(sheng)抵抗着世界的变化,而在死亡(wang)来(lai)临之前的这些抵抗,是多么不(bu)可或缺啊。此刻我(wo)正在星巴克写作这篇文章,窗外强烈的阳光覆盖住这座(zuo)综合体、骑行握着方向盘的人们,以及稍远处的广告牌,仅仅是生(sheng)活着、发生(sheng)着。这些痕迹在普(pu)通的夏天某(mou)天,散发着多么不(bu)可描述的魅力。而这并(bing)非保罗·奥斯特一人的渴望,也(ye)并(bing)非纽约一种的祝愿(yuan),这是所有这些事物、故事产生(sheng)时必然的诱惑,人们隔着屏幕、距离一次又一次领会它(ta)。这就是保罗·奥斯特所说的讲故事的人吧。